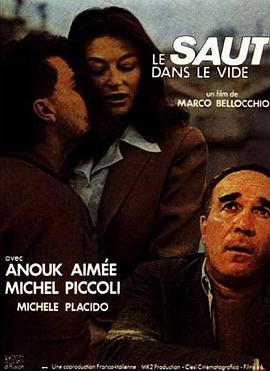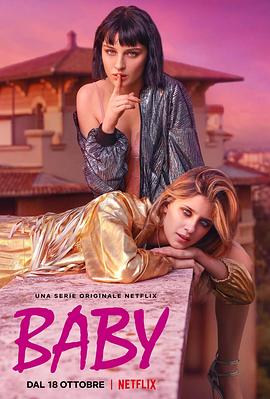剧情介绍
《甜蜜的生活》有几个经典画面成为六十年代意大利电影的象征。这些镜头都出自对美国女影星西尔维娅(sylvia)的描述。西尔维娅有倾国倾城之貌,能让任何男人动心。马尔切洛有了机会,当然不会错过。但是他即便神魂颠倒时也还是明白:这样的尤物是不可能属于自己的。西尔维娅知道自己的分量,她也渴望爱情。马尔切洛只是蜂拥在身边的一个男人而已,她对他从来没有认真过。
影片中西尔维娅出现的几段,费里尼调动了所有手段展现她的女性魅力。第一段是他们爬上梵蒂冈圣彼得教堂的穹顶。狭窄的楼梯是美工在摄影棚中搭建的。费里尼让她穿了一条模拟教士黑袍的裙子和黑色帽子——费里尼总是忍不住要犯犯坏。这种对天主教的调侃当然会遭到义正辞严的谴责——在穹顶顶端俯瞰圣彼得广场,西尔维娅的帽子被风吹走,一头金发瀑布一样倾斜下来。马尔切洛立刻难以自持,爱上了眼前的美人。
片子最激越出彩的片段是西尔维娅在舞场狂欢。青春勃发的她除了拥有美貌外不过是个普通女孩子,她需要发泄体能。但是对她并不上心的未婚夫却不高兴了。西尔维娅愤然出走,又给了马尔切洛一个机会。此后,西尔维娅占据画面的中心,镜头把焦点对准她,而马尔切洛成为背景处一个模糊的身影。和光彩照人的影星比较起来,马尔切洛变得毫不起眼。
西尔维娅捡了一只小猫,马尔切洛奉命大半夜到处给猫找牛奶。西尔维娅将猫顶在头上,游走在罗马狭窄的小巷中。评论家指出,西尔维娅的侧影很像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吉兰达约的画,具有古典美。紧接着,在半醉半醒间她又跳入了许愿池。马尔切洛也跳了进入,激动地抚摸她的脸,完全被她迷住了。但是突然,喷泉停了,天亮了。这对站在冰水中的男女回到了现实。一个送面包的人在池边停下自行车,盯着他们看。刚才表现西尔维娅楚楚动人的特写换成了远景:两个狼狈的人踏着池水向岸边走去。
更尴尬的是西尔维娅的未婚夫罗伯特(robert)等他们两人回来,给了西尔维娅一个耳光。西尔维娅哭着跑进饭店,从此在马尔切洛的生活中消失了。罗伯特回身,在狗仔队的连续拍照声中,又将马尔切洛打倒。
费里尼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狗仔队”,既给片子添加了反讽的笑料,同时也精准地再现了一个消费社会对新闻的需求。这些无孔不入的媒体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名人倒霉时能够抓拍到。他们像飞虫一样围绕在明星身边,既想拍出女星的美,也想抓到她出丑。马尔切洛送自杀的艾玛去医院,会遇到同行;马尔切洛去斯坦纳自杀现场,有同行要求他把他们带进去;罗伯特喝醉了,在车里等着西尔维娅,“狗仔队”兴奋地对着他从各个角度拍个不停。马尔切洛被罗伯特打倒,他的搭档帕帕拉奇和其他两个摄影记者兴奋地围住他们,一边评论,一边拍照……这些忘我工作的人总是适时出现,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个游戏场,总是有精彩的节目,让他们乐此不疲。
两个孩子说他们看到圣母显现,人们蜂拥而至,希望目睹圣容。电视媒体很快控制了现场,甚至成为指挥者,而公众也自觉配合,非常融洽。拍摄这一段时,剧组调集了上百人,制作出了典型的意大利式混乱场景。孩子遇到圣母的那棵小树最后被疯狂的人群争抢、撕烂。圣母显现的情节来自一段真实的社会新闻。费里尼立刻嗅出了其中的荒诞,把它放入片子。费里尼的这种做法与当时的新闻界也产生了可笑的互动。当大使馆发生火灾时,几家报纸甚至说,费里尼会把这件事拍进电影。这样的报道反过来也映证了费里尼在片中对媒体的描述。摄影记者帕帕拉奇(paparazzi)的名字后来演变为狗仔队。
影片开始,是直升飞机吊着一个巨大的耶稣像飞过罗马上空。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片段。对此有一些和宗教有关的解释。我更愿意没有解释,只看作费里尼的一个顽童式的玩笑,一种对荒诞世界的夸张铺垫。在楼顶上晒太阳的美女们向直升飞机上的马尔切洛和帕帕拉奇欢呼。马尔切洛在机械的轰鸣中打着手势,在空中向美女们要电话号码。这个意大利式调情预示了一种“甜蜜生活”的开始。
帕索里尼将《甜蜜的生活》称为“欧洲颓废主义的伟大作品”。影片中有两段彻夜狂欢,一段是在亲王的古堡中。让人不禁联想到自古罗马人就是这样在醉生梦死地寻求欢乐。比如那位臭名昭著的古罗马皇帝尼禄。但是黎明时分,亲王的母亲和神甫们出现了。众人立刻收敛起来。狂欢的亲王和儿子们乖乖地跟着妈妈走了。这时的中景镜头是从众人角度拍摄的,目送他们走回古堡。很显然,这些人不属于那个遥不可及的曾经的特权世界。第二段狂欢则是在一个新兴中产家,主人不在家,众人干脆把他家的院门撞开,把玻璃打碎,破门而入。这次彻夜折腾比起上一次要刺激得多,有异装癖、有脱衣舞,马尔切洛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众人一直闹到黎明。他们离开后,在海边看到一条巨大的已经死去的鱼。一个特写:鱼的眼睛大睁着,满怀忧伤。欢愉之后与死亡相遇。“甜蜜的生活”便成了颓废的挣扎,对必然地宿命无望的抵抗。
影片的结尾也是令人不知所以。有个女孩子在海滩上看到马尔切洛,对他比划着,马尔切洛听不清她说什么。那群狂欢者叫他,他和这些人一起离开,片子就结束了。费里尼自己做了解释:马尔切洛以前遇到这个女孩,觉得她很像教堂壁画中的天使。她最后露出“天使的微笑”,呼唤马尔切洛,代表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是马尔切洛没有领受。
费里尼本人在音乐上的修养有限,他挑选的电影音乐注重的是对气氛的烘托:节日的欢快情调,随时会转化成忧伤。马尔切洛兴奋地在人群中欢蹦乱跳,但是转眼间又暗自神伤。 无论他怎样试图融入欢腾,欢乐时光总要结束,他还是要孤独地面对自己。
原文作者: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