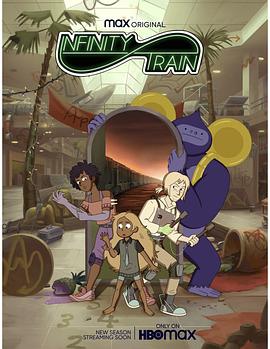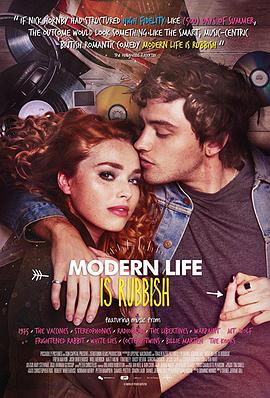剧情介绍
文章选自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
——庾信《哀江南賦》
一、前言
佛陀作爲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其生滅年代是近代世界佛教學研究的重大關切。由於印度本土歷史意識的淡薄,以及佛教南北傳、各部派記載的分歧,使該問題的解決困難重重。不過這一問題的挑戰,也恰恰是引起各國學者興趣的來源。1988年,世界各國的佛教學者在哥廷根召開了一次大會,形成了一些共識,基本上拋棄了南傳系統所主張,一度廣爲接受的長繫年[1],但確切的年數遠未定讞。
如果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便發現文獻所見諸說往往受制於複雜的宗教動機,問題的爭論與其說是歷史的探究,不如說是經典的解釋。先行研究已經對相關材料進行了梳理[2],本文主要關注中古佛曆推算的一類特殊文獻,即將佛誕(滅)年代[3]準確地換算爲華夏上古的王統紀年。在各種有關佛誕的言說中,這一形態顯然最爲複雜,它暗示了佛誕距今的總年數(稱爲“積年”),華夏上古紀年距今的總年數,有時還給出干支。這種將佛教歷史與華夏古史對接的努力,可以說是世界史編纂的雛形。佛曆推算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數字,數字塑造了人們的時間感受。
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各種學說不是紛然雜陳,而是存在著對話和衍生的關係;相似的結論,論證的方法卻迥然有異;不同的結論,論證的方法也可能遙遠地契合。總體來說,漢語佛教文獻中的材料對確定佛滅年代並無幫助,然而通過對其立論動機、論證技術的分析,頗可窺見中國中古時期知識精英的學術方法和淵源流變。因而也使我們對中古時期科學與宗教、歷史與現實關係的複雜性有更多的反思。
二、莊王十年說的確立及其缺陷
1. 經文的比附
南朝流行周莊王十年四月八日佛誕說。此說成立的依據是將《太子瑞應本起經》與《春秋》的記載加以比附。《瑞應本起經》在講述悉達多太子降生的情景時說:
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脇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
是時天地大動,宮中盡明。梵釋神天,皆下於空中侍。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湯,浴太子身。身黃金色,有三十二相,光明徹照,上至二十八天,下至十八地獄,極佛境界莫不大明。當此日夜,天降瑞應,有三十二種……[4]
立說者由此天地“莫不大明”的景象聯想到《春秋·魯莊公七年》的如下段落: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云: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預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5]
經云“恒星不見”,當是異常的天象記錄下來。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春秋》經文爲三傳所共有,《左傳》解釋的獨特之處有二,一是認爲“恒星不見”是夜明所致,而《公羊》、《榖梁》二傳對此皆無解釋;二是把“星隕如雨”的“如”字解釋爲“伴隨”,二傳則都認爲是“好像”,即流星雨[6]。杜預的解釋順著《左傳》的邏輯做了更加精細的排除,他首先推算出該日是四月五日,證明此時月光尚微,不足以掩蓋列星的光華。又推測當時或許也沒有雲彩,恒星不見,只能是日光至黃昏仍不衰弱所致。
我們看到,《瑞應本起經》記載佛陀降生四月八日之“大明”,最易比附於《春秋左氏傳》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使恒星不見之“夜明”,換算即爲周莊王十年。而杜預進而推算該年四月辛卯是四月五日,則與《瑞應本起經》不合。因此這種比附乃專依《左氏》而不依杜注。一旦杜注受到重視,便會產生解釋上的麻煩。
《太子瑞應本起經》是孫吳黃武初至建興中(222-253)支謙所譯[7],但將經文與《左傳》文字加以比附,卻是到南朝劉宋時期才出現的,這裏稍做考辨。劉林魁在南朝史籍中檢出莊王十年佛誕說9例[8],最早的3例是:
(1)唐人韓鄂撰《歲華紀麗》引謝承《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凈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9]
(2)宗炳《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10]
(3)《文選》李善注引顧微《吳縣記》: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11]
第1條材料的真實性存疑,留待下文詳論。第2條,《弘明集》載元嘉十二年(435)宋文帝與何尚之等論佛教事已經提到與宗炳的對談,其時必在是年以前。第3條《吳縣記》作者顧微,劉林魁先生說是三國時人,不知何據。今考此人撰有《廣州記》,其中所載地名,設置在劉宋元嘉十六年(439)至泰始三年(467)之間。可知其人是劉宋時人,與宗炳約略同時。另外顧氏既然說“佛法詳其始,而典籍無聞焉”,則之前的典籍沒有佛陀降誕於周王某年的明確說法,類似的比附當是劉宋元嘉年間興起的新說。
宗炳爲了回答何承天佛何以不開化邪見之徒的疑問,以經典中“恒星不見”之事,說明“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表面上看,宗炳舉出此例頗爲隨意,但必須注意宗炳撰《明佛論》和與何承天的對話中,都面對類似的疑問,即周、孔聖人之書中,何以不聞佛法開教之跡[12]?促使他創出這一新說的動因還在於回應儒學禮法之士對佛法在中土起源的追問。
2. 沈約與陶弘景的辯難
莊王十年佛誕說是南北朝時期的主流觀點,只有梁初的沈約對此提出了質疑:
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13]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14]
沈約提出兩點疑問,一是佛經所記四月,依據不同的建正之法換算,對應中土年月不同;二是上文所述,杜預注云四月辛卯是五日而非八日的問題。“長曆”當是指杜預所作《春秋長曆》[15]。
沈約發難的語境是與道士陶弘景討論《均聖論》。論中沈約提出“世之有佛,莫知其始”,進而把燧人氏變腥爲熟直至周公製禮作樂的文明演進,解釋爲佛法次第彰顯,開化生民的歷史。因此,他說佛法“唐虞三代,不容未有”,周初尚無記載“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也。”[16]這種漸進論的史觀是東晉南朝的流行思潮,最早可以上溯至孫綽《喻道論》,而在沈約這裏獲得了最集中的表達[17]。
陶弘景不同意沈約之說,他認爲“釋迦之現,近在莊王”,“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又談到秦漢以降的許多史實,如東方朔與漢武帝談劫灰、漢明感夢等等,并對其年代做了精細的排定。史載陶弘景撰有“《帝王年曆》五卷”,注云“起三皇至汲冢《竹書》爲正,檢五十家書曆異同共撰之也。”[18]其書雖已亡佚,然而《真誥》引《竹書紀年》凡三處,猶足以考見陶弘景之學術。《真誥·稽神樞》載堯時仙人展上公食白李,“憶之未久,忽已三千年”事,下注云:
諸曆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己卯歲(即東昏侯永元元年,499),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堯父,說此語時,又應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乎?《汲冢紀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彌復大懸也。[19]
作爲南朝一流的學問家,陶弘景在上古的年代推算上下過一番功夫,其學兼採諸家曆法,而特重《竹書紀年》。在佛道相爭最爲激烈的唐初,陶弘景《年曆》被護法僧人法琳援引以支持自說[20],不難想見其學術之客觀及立場之中正。
陶弘景集諸家年曆討論佛誕年代有一個背景,即梁武帝對此問題的興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梁武帝本人曾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今佚。惟《史通·六家篇》云:“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21]。“太初”自是意指上古,《梁書·吳均傳》及《隋書·經籍志》皆云“上起三皇”[22]。《通史》中是否有佛陀降誕的內容,史無明記,但從庾信《哀江南賦》“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23]之語可知,《春秋·左傳》“恒星不見,星隕如雨”之事,必是武帝重雲殿與群臣講議的重要內容[24]。考慮到武帝對佛教的熱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佛陀降誕會被寫入《通史》。陶弘景的《帝王年曆》也是這一文化風氣下的產物。
反觀沈約的質難,則破大於立,猶承兩晉清談之餘習。其目的在於破壞《瑞應本起》與《春秋》經文的聯繫,因此從多個角度同時發難,最終維護“世之有佛,莫知其始”的不可知論,對於年代推定則并無嚴肅的關切。《廣弘明集》不載陶弘景的進一步回應,以沈約的勝利告終。沈約的問題真正得到回應,要等到北周釋道安和隋代費長房出現。
回顧南朝的佛陀年代推定,我們看到,立說的基礎是《瑞應本起經》和《春秋左氏傳》祥瑞記載的比附。學說興起的時代約在劉宋元嘉年間,目的是在儒家經典中找到佛陀誕生的痕跡,以此回應儒家的質疑。到了梁初,在武帝崇佛興學的背景下,這一問題的討論趨向精密化,經文比附的缺陷也開始顯現出來。《春秋》“四月辛卯”和《瑞應本起》“四月初八”到底能否勘合,成爲此說成敗的關鍵。
三、莊王十年說的精密化
1.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帝年》
梁武帝和陶弘景的佛陀年代推算,雖然可以從文學作品和《廣弘明集》中約略窺見,終究難知全貌。費長房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則要豐富得多。隋開皇十七年(597),翻經學士費長房撰成《歷代三寶紀》,全書十五卷,卷一至卷三爲《帝年》,編製了一個從周莊王九年佛陀入胎到開皇十七年的通史大年表,配以干支[25]。這是佛教史學編纂史上的創例。第四至十二卷爲代錄,開列各代譯經書目和譯人小傳。小傳的部分也有與佛誕有關的記載。
《帝年》在莊王十年條下,費長房羅列了佛誕年代的五家學說,分別是:
(1)東晉法顯說;(2)北齊法上說;(3)《像正記》說;
(4)北周道安說;(5)《眾聖點記》說。
其中(1)、(3)、(5)是求法、傳法僧傳來的印度學說,(2)、(4)則出於周、齊僧人之推定。值得注意的是,費長房本人雖然在此接過道安的說法加以修正,最終將佛誕繫於周莊王十年,但並沒有駁斥其餘的四家,反而將他們各自給出的積年,換算到了開皇十七年。
我們以《歷代三寶紀》卷一《帝年》的敘述爲基準,簡單核算一下費長房對印度傳來三說數據的處理,便發現不少問題。
○法顯說:
依《法顯傳》推,佛生時則當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至今開皇十七年丁巳便已一千六百八十一年。[26]
《法顯傳》記載法顯在師子國(今斯里蘭卡)出佛齒遊行之前,僧人唱言:“(佛陀)在世四十五年說法教化,……眾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歲。”章巽先生考證,法顯此時在師子國,爲義熙六年(410),由此推算佛滅年代在公元前1087年[27]。但對於費長房的推算,重要的是他自己怎樣判斷法顯聽聞此事的年代。《歷代三寶紀》卷七引錄此說之後,加了一段案語,云“時正當晉義熙元年(405)……計從義熙元年太歲乙巳,至今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便成一千六百八十一載矣。”[28]
如果費長房把佛滅年代當成佛誕,則至開皇十七年爲1497+597-405=1689年。《法顯傳》原文說釋迦“成佛在世四十九年”,三十成道,則壽數實爲79歲;費長房節引作“如來在世45年”,則壽數僅爲45歲。無論哪種算法,所得均與費長房給出的1681年不合。唯一的可能是認爲義熙元年是“九年”(413)之訛,則佛滅至開皇十七年之積年1497+597-413=1681年。然而文中又明確說義熙元年干支爲乙巳。最合理的解釋是,費長房先是把佛滅當成了佛誕,又以義熙九年匆忙核算了積年,最終又將義熙九年認作元年,給出干支。推算的過程可謂極其混亂。
○《像正記》說:
依《像正記》:當前周第十七主平王宜臼四十八年戊午,至今丁巳,則一千三百二十三年。”[29]
案:《法經錄·佛滅度後撰集錄》著錄“《像正記》一卷。”[30]云是此方佛法傳記。從書名上看,應是記載正法、像法年數的史書。《歷代三寶紀·帝年》還有兩處引用了《像法正記》,兩處引文如下:
如來滅後二十餘年,長老迦葉住持法藏,付囑阿難,然後入滅,出《像法正記》。
迦葉滅後二十年,阿難住持法藏,然後付囑末田地,方始入滅,亦出《像法正記》。[31]
除此以外,雖然沒有指明出處,但隨後兩處引文:“末田地滅後,舍那婆修住持法藏亦二十年,付優波掘多,然後入滅。”和“舍那婆修滅後,優婆掘多住持法藏亦二十年,付提多迦,一名尸羅難陀,然後入滅。”[32]結構完全一致,當是同出於《像法正記》。前引“長老迦葉”條校勘記云,高麗藏以外諸本《像法正記》均作《像正記》。因此基本可以認爲《像法正記》就是《像法記》。綜合這些情況,我們判斷《像法記》的內容是如來入滅以後僧團領袖歷代相承年數的一份記錄,其結構類似《付法藏因緣傳》或禪宗祖師譜系。費長房根據此書所給出的年代上推,將佛陀生年換算到東周平王四十八年。
○《眾聖點記》說:
依趙伯林梁大同元年(535)於盧山遇弘度律師得佛滅度後《眾聖點記》推,則當前周第二十九主貞定王亮二年甲戌,至今丁巳(597)殆一千六十一年。唯此最近。准三藏教及《善見律》云:佛何以不度女人?爲敬法故,正法千年。以度女人,減五百年。制修八敬,還滿千年。然後像法亦一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來學三達智,并得四果。六千年去,學不得道。萬年已後,經典文字自然滅盡。但現剃頭有袈裟耳。正法之世,大乘味淳。至乎像代,味少淡泊。若入末法,則無大乘。奴婢出家,污染淨行,惡王治世,課稅僧尼。今則未然,緣此正像交涉未深,三寶載興,大乘盛布,寧得已接於末法者哉![33]
《善見律毘婆沙》(pali.samantapāsādikā)是錫蘭大寺派覺音(buddhaghosa)對巴利律藏的注釋[34]。《歷代三寶紀》卷一一《南齊錄》更詳細地記載了《善見律》譯出及傳播的經過:
師資相傳云:佛涅槃後,優波離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華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三藏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舶反還去,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488)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此《善見毘婆沙》,因共安居。以永明七年(489)庚午歲七月半夜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華供養律藏訖即下一點,當其年計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
趙伯休梁大同元年(535),於廬山值苦行律師弘度,得此佛涅槃後眾聖點記年月,訖齊永明七年。伯休語弘度云:“自永明七年以後,云何不復見點?”弘度答云:“自此已前,皆是得道聖人手自下點,貧道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不敢輒點。”伯休因此舊點,下推至梁大同九年(543)癸亥歲,合得一千二十八年。房依伯休所推,從大同九年至今開皇十七年(597)丁巳歲,合得一千八十二年。
若然,則是如來滅度,始出千年。去聖尚邇,深可慶歡,願共勵誠,同宣遺法。[35]
按照這一派的傳說,佛滅以後,從優波離纂集律藏開始,僧人每年七月十五日夏安居結束,便以香火增添一點,作爲紀年標記,歷世相承,稱爲《眾聖點記》。其中給出的師資相傳譜系,亦見律文《舍利弗品》[36]。
律本之譯出,《出三藏記集》載有出經記,云僧伽跋陀羅與僧禕(同書卷二作“僧猗”)在廣州竹林寺,此後僧伽跋陀羅返回天竺。而按照費長房的說法,則似乎攜來經本的是僧伽跋陀羅的老師,以“今三藏法師”稱之,具體所指不明。律本譯出以後,依經記,是淨秀尼[37]發願請“憑上”抄寫,永明十一年(493)傳至建康。
巴宙指出,趙伯林大同元年在廬山弘度律師處見到的律本,從永明七年譯出以後即不再點點,而據淨秀尼所述,“仰惟世尊泥洹已來年載,至七月十五日受歲竟,於眾前謹下一點,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38]則似乎律本在永明十年仍在加點,因而主張將點記增加3個點數,計爲478,再以此推算佛滅年代[39]。這顯然是一種誤解。首先,淨秀在律本上加點,並非永明十年,而是永明十一年。更重要的是,淨秀拿到的是抄寫到建康的複本,而趙伯林所見則很可能是梁末由廣州傳至廬山的原本,在複本上依舊加點,和對原本“奉持頂戴,不敢輒點”,兩者並不矛盾,也互不干涉。
巴宙的研究最重要的提醒是對點記傳說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他指出,如果是優波離所傳,被攜至錫蘭,則必被奉爲聖物。而南傳典籍毫無記載,法顯當年遊歷,亦未涉及。其實早在唐代,智昇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此墨點記與法顯所傳師子國佛牙精舍唱記年歲全懸,此云優波離集律藏竟自恣了已,手自下點,年年如是。展轉相付,流傳至今者。此或不然,尋此《善見婆沙》,非是波離所集,乃是部分已後二十部中,隨彼所宗,釋一家義,撮要而解,非全部毘尼也。即此撰集已後,年下一點,此或如然。若言波離手自下點者,未可即爲指南也。[40]
因此說到底,眾聖點記是否可以作爲佛曆推算的可靠史料,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檢討。
我們這裏關心的仍然是費長房的推算和立場。趙伯林首先從永明七年的975點下推至大同九年,得到975+(543-489)-1=1028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廬山得遇此本是大同元年[41],這裏推至大同九年,很可能是考慮該年爲癸亥年,一甲子的結束。費長房以此再下推,至開皇十七年,凡975+(597-489)-1=1082年[42]。反觀前引《歷代三寶紀》卷一《帝年》中給出的1061年,既與《南齊錄》依點記推算出的佛滅年數不同,即便減去佛陀在世的80年,折算成佛誕年數,也不能相合。
由此我們發現,費長房對舊說的整理是分步進行的,《代錄》的記載比較詳細,推導過程也比較清晰。《帝年》的說法不僅相對簡略,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可知,錯誤往往更多。他對法上和道安學說的處理中也呈現出這種規律。《代錄》應該是費長房得到的原始記載,而《帝年》則是《歷代三寶紀》成書前夕匆忙製成的。
前文業已指出,費長房雖然以道安說爲基礎考定佛誕年代,但卻沒有拋棄或反駁其餘四家。這樣做的目的很可能是爲了反駁當時已入末法的流行學說。末法思想是中古佛教史上的重大問題,這裏不能展開,只想強調其中的兩點。第一,研究者指出,雖然“末法”一詞在早期的經典和石刻史料中已經出現,但只簡單意味著佛法衰頹的世界,與正、像二法並列,構成三時的整體時間架構,是在較晚的時候出現的,迄今爲止,並未找到梵語佛典的對應文本。第二,正、像、末三時的時間跨度,經典中講法不一,尤其在“末法”成爲一階段以前,有正法五百、像法五百;正法五百、像法一千;正法一千、像法五百各種學說。漢地接受三時說最著名的南嶽慧思《立誓願文》、三階教信行的《三階佛法》以及房山雷音洞靜琬的刻經記,基本上都接受了正、像二法總共1500年的說法[43]。
【圖1-雲居寺刻經窟(作者拍攝)】
費長房刻意選擇在“眾聖點記”條下發揮對末法問題的看法,不僅因爲諸說“唯此最近”,更重要的是,載有“點記”的《善見律毘婆沙·舍利弗品》給出的是正法一千,像法一千,末法萬年的時間跨度[44],這樣“點記”的1082年自然是“正、像交涉未深”之時,其餘四種算法也都沒有逾越佛滅兩千年的大限。這正是費長房想要論證的,大隋“三寶載興,大乘盛布,寧得已接於末法者哉!”
2. 道安、費長房對南朝傳統的發展
在五家舊說中,費長房最看重北周道安的《二教論》,他關於佛誕年代的討論是在道安學說的基礎上修訂而成。
《二教論》見於道宣撰《廣弘明集》[45],《歷代三寶紀·北周錄》亦有節引。兩書記此文寫作年代不同,考慮到《歷代三寶紀》時代較早,姑從其說[46]。北周天和四年(569),周武帝集群臣論佛道二教,甄鸞上《笑道論》,群臣議以爲不可,於殿上以或焚之。“至九月,沙門釋道安慨然遂纂斯《二教論》,以光至理。”該論的主旨是繼承甄鸞的觀點,維護佛教,貶抑道教,佛教的起源自然是論證的話題之一。文中“慧光遐炤,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以之神夢”句下,有注云:
《春秋左傳》曰:“魯莊公七年,歲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即周莊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王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災也。”案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
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47]用《魯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並與《春秋》符同。
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至今[48]一千二百五年。[49]
我們注意到,道安給出的典據,外典方面《春秋左傳》之外,還有《莊王別傳》,從行文風格來看,讖記的色彩十分明顯,它用卜筮的方式進一步指實恒星不見,夜放光明的原因是佛陀出世。
內典方面不言出自何經,但言佛二月八日生,成道亦在此日,這是比較特殊的理解。在漢傳佛教傳統中,存在三個佛誕日的日期,分別是二月八日、四月八日和十二月八日[50]。其中四月八日說最爲流行,支持此說的經典甚多,比如上文談到的《瑞應本起經》。十二月八日說則是宋以後出現的,此前未見。支持二月八日說的經典,最著名的是《長阿含經·遊行經》末尾的偈語“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八日取涅槃。”[51]此外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下文所引隋代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並同。
除了佛誕日期不同,道安還認爲《左傳》記載的那次夜明不是佛陀降生時,而是佛陀成道之時(也是二月八日)。爲了解釋佛經中的二月八日,相當於《左傳》中的四月辛卯,道安做了兩點論證。
第一是建正的問題。歷史上的朝代一般用夏正,即以雨水所在的寅月爲歲首。周代則以冬至所在的子月爲歲首,即以農曆十一月爲正月。道安認爲,天竺曆法用夏正,而《左傳》記載周代之事,自然用周正。這樣《左傳》所書之四月,就相當於佛經之二月。
第二是干支推算的問題。杜預注明確說此日是四月五日,道安則與董奉忠更用《魯曆》和《前周曆》推算,最終以後者推得辛卯正當八日。案,《魯曆》和《前周曆》都是《漢書·律曆志》所述六種古曆之一[52],其基本數據見於《開元占經》卷一〇五“古今曆積年及章率”。現代學者也據此做過復原,結論稍有不同[53]。今暫存疑。道安的推算過程雖不可知,但他通過曆法上的討論,正面回應了南朝沈約提出的兩個疑問,從而維護了使佛經與《左傳》經文的比附。
費長房繼承了道安關於建正和干支推算的所有成果,只對道安的判斷做了一點修正。他把《莊王別傳》中“西域銅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這句話中的“出世”,理解成如來誕生,而不是像道安理解爲成道。諸家佛傳類經典均記載佛陀三十成道,這樣推算下來,費長房的佛陀年代就比道安的結論下推了三十年:
佛以莊王九年癸巳四月八日,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國迦毘羅城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右脇。是時諸天影潛衛從,胎藏祕隱,世眼罕知。十年仲春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毘園波羅樹下右脇而誕,生相既顯,故《普曜》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左傳》說:“恒星不現,夜明也。”《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子生。”故《左傳》稱:“星隕如雨”。《本行經》說:“虛空無雲,自然而雨。”杜氏注解“蓋時無雲”。《左傳》又稱:“與雨偕也。”然《姬周曆》十一月爲正,言四月者即今二月。辛卯五日,魯史爲謬。沙門道安著《二教論》,用《姬曆》推,還合八日。唯以生時爲成道歲,遂令佛世遠三十年耳。[54]
道安排除了經文比附的障礙以後,費長房進一步引用《普曜經》和隋代新譯《佛本行集經》的有關經文,進一步附會《左傳》、杜預注中祥瑞描述。原先佛經與《左傳》的偶合只在於星隕、夜明兩種異象。上文談到,《左傳》對“星隕如雨”的“如”字做了與《公》、《榖》二家截然不同的解釋,“如”訓作“而”。費長房把它和佛陀誕生時“虛空無雲,自然而雨”的瑞相聯繫起來,充分體現了一流解經家的技藝。
費長房的工作還不止於此,《歷代三寶紀·帝年》在佛陀生年以後,還根據佛經中的零散記載,排定了佛陀一生的年譜。特別是,他對阿育王造塔這件佛教史的大事也做了排定。费長房自稱,根據《阿育王傳》載,“佛泥越後百十六年,閻浮提王名阿輸伽,出東天竺治華氏城,收佛舍利,散起八萬四千寶塔,匝閻浮提”[55],將此事排在周敬王二十六年。關於阿育王距佛滅時的年數,早期的佛典,包括費長房這裏所舉的《阿育王傳》,給出的都是一百年的約數,116年之確數僅見於真諦譯《十八部論》[56]。能在真諦的新譯中敏銳地抓住這一信息,其學問之精博也令人稱歎[57]。
如果僅從結論與核心論據來看,費長房仍然維持了南朝流行的莊王十年佛誕說。但經歷了北周道安和費長房的兩次發展,學說的組織大大豐富了,論證日趨精密。道安的主要貢獻是解決了沈約提出的有關建正和干支的疑問,使得佛傳經典與《左傳》經文得以對接。費長房則在此基礎上,牽合更多經典,將其排定在華夏王統紀年中,製成了一個上起周莊王九年(佛陀入胎之年),下迄開皇十七年的大年表。此後宋代的編年體佛教通史如《佛祖統紀·法運通塞志》等,其體裁皆肇端於此。
四、昭王二十四年說的譜系
基於《左傳》記載的莊王十年佛誕說,雖然經歷了南朝至周隋兩代的發展,漸趨精密,然而儒、佛經典的表述不同,畢竟給闡釋帶來了不少障礙。唐代以後,佛誕年代的主流說法是基於《周書異記》的昭王二十四年說。考察同時的文獻,可以看到當時流傳著幾種結果近似的推算。這些學說產生於北朝末期直到唐初佛道鬥爭白熱化的氛圍中,僞託十分普遍。因此首先要通過史源學分析排定其成立之先後,在此基礎上考慮其產生的原因及其衍生規律。
1. 成立年代之排定
昭王系佛誕說最早、最可靠的文獻是北齊沙門統法上之說。武平七年(576),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派遣使者到鄴城,問“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法所傳。”[58]法上的回答除見於《續高僧傳·法上傳》以外,最早的出處是《歷代三寶紀·北齊錄》和上文討論的《歷代三寶紀·帝年》,《歷代三寶紀·北齊錄》的記載比《續高僧傳》還要詳細。
《續高僧傳·曇無最傳》的記載需要稍加辨析。據傳文,魏正光元年(520),孝明帝召僧人曇無最與道士姜斌論釋、老先後。曇無最引《周書異記》和《漢法本內傳》,證明佛在老子之先。姜斌又引《老子開天經》,“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上奏,認爲此是僞經。詔姜斌流放馬邑[59]。這段所述的故事比法上年代更早,然而頗多疑點。蕭綜本仕南朝,叛降北魏是在孝昌元年(525),其他人物如魏收、溫子昇等,任官年代皆與正光元年不合,學者已指其僞妄[60]。
今考此事與故事中所引的《周書異記》,其第一次出現都是在法琳所撰《破邪論》中。此書是針對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的《上廢省佛寺僧表》而作,書首有武德四年、五年的上啓,因此認爲曇無最和《周書異記》說成立的下限都是《破邪論》寫作完成的武德五年(622),當無問題[61]。
在《破邪論》之後,法琳還撰有《辯正論》。其書卷五引述了隋代姚長謙的學說,並做了考辨。案姚長謙,名恭,北齊時曾爲渡遼將軍,隋爲修曆博士。其授業弟子傅仁均,即唐初著名的反佛鬥士太史令傅奕。開皇五年(585)長謙被召修曆,廣引眾書,撰成《年曆帝紀》四十卷[62]。這可以視作姚長謙學說成立的下限。
《辯正論》的成立過程也大致可考。武德九年(626)道士李仲卿作《十異九迷論》,劉進喜作《顯證論》,合力抨擊佛教。當年五月,唐高祖下《沙汰僧尼詔》。六月發生了玄武門之變,太宗李世民登基,敕令不了了之,然而佛道之間的緊張關係并沒有絲毫緩解。在這種環境下,法琳撰《辯正論》,對道教的批評做全面回擊。此書也是陸續寫成的,其主體部分完成於貞觀六年(632),最後完成時間應在貞觀九年至十年之間(635-636)[63]。李猛最近的研究指出,《辯正論》卷八收錄了法琳《與上述右僕射蔡國公書》,內容是向時杜如晦借書,“意者但是諸子雜書,及晉宋已來內外文集,與釋典有相關涉處,悉願披覽。謹以別錄仰呈,特希恩許。”[64]《辯正論》較之《破邪論》,徵引更爲淵廣,引入了姚長謙之說,應當便是藉助了杜如晦代爲徵集的藏書[65]。
代表法琳對佛誕問題的思考最後階段的是《法琳別傳》。由於在《辯正論》中揭露了李唐王室并非老子後裔,惹惱了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十月,詔刑部尚書劉德威等審理此案。十一月,太宗又親自責問。翌年,法琳流放益州,死於道中。僧人彥琮“每以琳公雅作,分散者多,詢諸耆舊,勒成卷軸。分爲上中下,目之爲《別傳》。”[66]《法琳別傳》觸及唐室忌諱,遭到了官方禁毀,但在地方仍然流行不絕,不僅《高麗藏》入藏,爲今《大正藏》本之底本,敦煌遺書中也有5件寫本[67]。此書雖然題爲《別傳》,實際是法琳遺著的集成。特別是卷中和卷下的前半,就是貞觀十三年法琳的獄中訊問筆錄[68]。
圖2-敦煌本《法琳別傳》
綜上所述,我們把諸說成立的年代下限做一排列:
法上說 武平七年(576)
姚長謙說 開皇五年(585)
曇無最、周書異記(破邪論) 武德五年(622)
辯正論 貞觀六年至十年(632-636)
法琳別傳(卷中、卷下) 貞觀十三年(639)
2. 昭王系佛誕說的發展歷程
昭王系諸說把佛誕年代提早了數百年,從莊王說到昭王說的移動,頗可尋繹其演進的過程與規律。本文有三點觀察。
(1)昭王系學說起源於北齊
最早主張佛誕生於昭王時代的是法上。法上自東魏起,終北齊一代,任最高僧官昭玄大統近四十年,他對高句麗使者的回答應該可以代表北齊官方的學說。僧傳說他“偏洞算數,明了機調”[69],估計對此問題做過一番考慮。其後姚長謙的《年曆帝紀》雖然作於隋初,但考慮到他先曾任北齊渡遼將軍,其學問蓋亦淵源於北齊。
另外需要注意,魏收的《魏書·釋老志》云:“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550),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70]魏收的推算與南朝流行的莊王十年差了一年,立論的依據則仍然是《春秋》經文。
從550年到576年,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裏,產生了新的學說,其原因很可能還在於北齊佛道相爭的語境。北齊天保年間發生過一次佛道論爭,法上派出了弟子曇顯與道士鬥法,《續高僧傳·曇顯傳》的記載提及陸修靜從梁入北齊,及梁武帝天監三年捨道歸佛等事,與史實不合[71],應有僞托增飾的成分。但史書還記載法上有弟子法存,“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靈裕并爲之作傳[72],這樣看來,在北齊創建伊始,佛道的關係已然比較緊張,當無可疑。法上將佛陀的年代從莊王十年,上推到更早的昭王二十四年,應當是希望使佛陀的誕生居於老子之前。
(2)從正經到僞史
法琳以及《續高僧傳》僞託曇無最之說援引的核心論據是《周書異記》,其成立的過程是本文最感興趣的。從行文風格看,《周書異記》是佛教徒撰作的僞書無疑。僞書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回顧莊王十年說的發展,我們看到南朝時期作爲立論依據的只有《左傳》。到了道安那裏,爲了增添論證的說服力,又加入了一種《莊王別傳》。傳文依托卜筮之語,將祥瑞的起因講得更爲明確。《左傳》的引入是爲了回應儒學正統人士的質疑,對論證佛教“古已有之”具有權威性。但儒家經典歷代相傳,歷代注家各有解釋,要與佛經加以比附,需要高超的解經技巧,排除各方的質疑,這并不容易。於是《莊王別傳》一類讖記類的作品就應運而生了。它努力營造經典中的人物和故事氛圍,同時按照佛教徒想要的樣子,將可資比附的信息傳達得更爲清晰。法上說根據《歷代三寶紀》腳註,乃“引《穆天子別傳》爲證。”[73]從下文所引法上之說,敘事與《周書異記》多有出入,知爲兩書。
《周書異記》也是同一性質的作品,文字的鋪陳較《莊王別傳》和《穆天子別傳》更加繪聲繪色,表達也更爲直白:
①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並皆溢出。宮殿入[74]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在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蘇由曰:“即時無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人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②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非周道所宜,即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攘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③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將滅度,朕何憂也。”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75]
不過僞作應該仍然依托正典而加以踵事增華。明顯可以看出,《莊王別傳》是《左傳》魯莊公七年的影子作品。而《周書異記》之所本,許理和已經指出,《古本竹書紀年》中有塗山之會的描述,這一情節在《周書異記》中也有反映,後者或許是以前者爲藍本[76]。觀察上節的引文,我們還發現,情節①和③分別爲了論證佛陀的誕生和入滅,偏偏只有講述塗山之會的情節②對應的年代是“佛久已處世”,顯得不倫不類。筆者推測,這恰恰反映出《周書異記》作僞之脫化未盡。
(3)從干支到王統紀年
再觀察昭王系諸家學說的表述形式。
法上說:
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576)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77]
此外《續集古今佛道論衡》還記載了法上說所推佛滅年代:
齊國大統法師達摩欝多羅答高黎國諸法師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當周孝王五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78]
《周書異記》已見上引,關鍵的信息是:
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佛誕,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佛滅。
曇無最說:
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79]
姚長謙說:
佛是昭王二十六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原注:至開皇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六載矣。[80]
以上諸說,除曇無最說以外,都以王統紀年+干支的形式表述。姚長謙說與《周書異紀》在王統紀年的推算上差1-2年,但干支相同。法上說雖然引據《穆天子別傳》,對佛滅年代的理解不同,但在佛誕年代的說法上,三家學說一致認定是甲寅年。這樣的種種跡象表明,此前或許有一種僅以干支表達的佛陀生滅年代表述,諸家分別據此推算,得出了不同的王統紀年。
這樣推測的理由一是考慮到中古時期讖緯流行,而讖緯的最大特色在於將所要傳達的信息控制在顯隱之間。如果過於顯白,則會失去神秘感;過於晦澀,則會失去號召力。因此在讖記類的表達之中,干支紀年十分流行。東漢末年黃巾起義,以“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作爲號召。佛教方面,道宣記載道安在襄陽造丈六佛像,銘文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81]從太元十九年經歷三個周天甲子,正當北周滅佛的建德三年。可見佛教的讖記也受這一傳統影響。
二是我們在現存作品中確實看到了純以干支表述佛陀生滅年代的例子,這就是南嶽慧思的《立誓願文》。這篇文字是這樣開頭的:
我聞如是,《釋迦牟尼佛悲門三昧觀眾生品本起經》中說:“佛從癸丑年七月七日入胎,至甲寅年四月八日生,至壬申年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至癸未年年三十,是臘月月八日得成道。至癸酉年年八十,二月十五日方便入涅槃。
正法從甲戌年至癸巳年,足滿五百歲止住。像法從甲午年至癸酉年,足滿一千歲止住。末法從甲戌年至癸丑年,足滿一萬歲止住。”[82]
願文引據的《悲門三昧觀眾生品本起經》,竟然以干支紀年給出年代,必是僞經無疑。不過最令人玩味的也正是這種奇特的表達。這種純以干支紀年的方式,可能就是昭王二十四年說的雛形。到了知識精英手裏,就被用各種通史年表,折算成了周代某王某年的形式。而曇無最的故事裏,其表達又省去了干支紀年,只留下推算得出的王統紀年。
最後再來辨析開頭提到的《歲華紀麗》引謝承《後漢書》。他說“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寄生于凈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可以看出,此說在王統紀年上遵循莊王十年之舊說,但又在干支的表述上沿用了昭王系學說,以甲寅爲佛誕。因此筆者推斷,這是在莊王、昭王兩系學說成立之後,以二者而前提,糅合二者創立的學說[83]。
綜上所述,起源於山東北齊的昭王二十四年佛誕說,可能與佛道鬥爭和末法思想皆有或多或少的關聯,佛道鬥爭是佛誕年代提前的直接動機,而所引起的末法焦慮則是其影響。強烈的宗教訴求使其徹底拋開了表述曖昧模糊的儒家正經,轉而尋求《周書異記》一類雜說僞史。其最初的雛形可能是簡單質樸的干支紀年表達,經由知識精英的推算,轉換成多種王統紀年。爲了掩蓋《周書異記》的僞撰性質,法琳又炮製出了曇無最在北魏正光二年引用此書的故事,將新撰的僞作推到較早以前。然而故事到此還沒截止,法琳在最後的日子裏,還建構了更宏大的體系,企圖將南朝、周、隋一系的莊王十年佛誕說包攝其中。
3. 對費長房說的揚棄
貞觀十三年,法琳以謗訕朝廷下獄,刑部尚書劉德威等就《辯正論》所說逐條訊問,《法琳別傳》卷中記錄了關於佛誕說的進一步申述。其中談到費長房的學說:
又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恒星爲驗,而云佛生。未悟恒星別由他事。琳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84]
前文談到,無論費長房的莊王十年說,還是法琳的昭王二十四年說,其立說的根本方法都是祥瑞的比附。而佛陀一生從入胎至滅度,數度“放光”。費長房正是利用此點,將道安理解的“成道”之放光,變成“降生”之放光。法琳這裏運用的是同一方法,他利用《文殊師利涅槃經》記載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菩薩涅槃前的放光,爲《左傳》莊王十年的時點找到了對應,從而揚棄了費長房的立論,將佛誕日提早250年。
但是,法琳之淵博并沒有超越費長房,他所援引的《文殊師利涅槃經》,費長房也關注到了。案此經今存[85],今本經文云:
如是大士久住首楞嚴,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宣暢敷演十二部經,教化成熟五百仙人,令得不退轉。[86]
費長房將此經排在西漢文帝後元四年(前160),去佛滅正好450年。[87]法琳要想以昭王二十四年爲佛誕,同時將舊有的莊王十年囊括進來,經文450年的時段無論如何顯得太長,於是對經文做了改動,將這一時段縮短爲250年。值得注意的是,法琳本人較早完成的《破邪論》中引到此經,原作“四百五十年”[88]。可見“二百五十年”之文確是法琳晚年所做的改竄。
五、結論
回顧中古時期佛誕年代推定的討論,我們驚異地發現成爲古代佛教學術主流的莊王十年和昭王二十四年兩說,論證的前提都是承認佛陀誕生時的放光真的可以周遍世界,因而可以在華夏上古的記錄中找到印證。以今日科學的眼光觀察,從如此荒謬的前提出發,所做的一切論證都是無效的。然而這種努力使本國的歷史與作爲世界宗教的佛教之歷史得以銜接,某種程度上催生了一種佛教版的世界通史,又不得不說是一種偉大的創舉。
本文的工作并非抽象地肯定或否定中古時期的相關討論,而是希望在紛然雜亂的學說之間,梳理出兩個系統的衍生史。根據本文的考察,南朝、周、隋一系的莊王十年說與北齊、初唐一系的昭王二十四年說,兩說立論的動機頗有不同,其衍生的模式有同有異。前者爲了回應儒學的質疑,必須於六經典墳中發現佛陀,證明佛教之於古有徵,因而援引《春秋》。後者則是佛道相爭所致,爲了在技術上擺脫經學的束縛,索性炮製了《周書異記》一類的僞史。前者因有經典依據,最初以王統紀年的形式表述,困難在於與佛經的勘合。後者最初以干支的形式表述,因此在周代王統紀年的比定中出現了各種結論。
拋開各家推算的結論,以此一端審視各時代知識精英的學術方法,也各呈異趣。南朝學術最純,絕少引書,辨名析理,議而不斷。北周道安之學最精,在技術上排除疑難。隋費長房之學最博,牽合眾多經典,扶翼一家之說。外表結構整飭,演算則屢屢失誤,學說亦少發明。至唐初法琳之學,則感於意氣,頗嫌蕪雜。且學說前後不一,處於激烈變化之中,始則《破邪論》拋出《周書異記》,至《辯正論》又發掘姚長謙之說,晚年又企圖融攝費長房之學,乃不惜竄改經文。
經過法琳的表彰,道宣《廣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智昇《續古今佛道論衡》,乃至8世紀後半的燈史《曆代法寶記》[89]皆援引《周書異紀》,昭王二十四年佛誕說漸漸取代了莊王十年說,成爲教團知識的主流。然而結論的背後,曾有繁複的論證和學說間的對話、競爭,展示了中古學術史上頗具異彩的一頁。
編者按:原載《文史》2018年第4期,第117-138頁。個別文字稍有修訂。
*說明:本文所引的佛教文獻,均出自cbeta2016版,數字分別表示《大正新修大藏經》的冊數,經號,頁碼,上中下欄以及列數。文字如無特殊情況,從《大正藏》底本《高麗藏》。若底本有誤,則參考其他藏經版本擇善而從,并加說明。對於已出版單行校訂本,標注單行本的頁碼。
[1]哥廷根大會的成果結集爲三冊論文集,heinzbechert, ed. the dating of the historicalbuddha. die datierung des historischen buddha, i-iii, vandenhoeck & ruprecht gmbh & co kg, 1991-1997. 對佛滅年代問題的系統梳理,參見紀贇《佛滅繫年的考察——回顧與展望》,《佛學研究》第20期(2011年),第181-200頁。
[2]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和僧界對佛滅問題的研討,參見《佛滅紀年論考》(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97冊)。張總先生還考察了中國境內石刻所見佛滅年代,列舉了數十種異說,參見張總《末法與佛曆關聯初探》,《法源》第17期,1999年,第128-148頁;《末法與佛曆關聯再探》,《法源》第21期,2003年,第195-214頁。
[3]相傳佛陀八十歲入滅,這一點在各種佛教經典中無大分歧(偶爾相差一年),因此佛誕與佛滅,知其一只需上推、下推80年便可得到另一年代。爲行文方便,當泛指佛陀生卒年時,以佛誕稱之。
[4]《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一,t03, no.185, p. 473, c1-9.
[5]《春秋左傳正義》卷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63-264頁。
[6]《公羊》、《榖梁》二傳經文“夜”作“昔”。
[7]蘇晉仁、蕭煉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華書局,1995年,第28頁。
[8]劉林魁《〈廣弘明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75-179頁。
[9]韓鄂《歲華紀麗》卷三,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頁上。
[10]《弘明集》卷三,t52, no. 2102,p. 21, a19-20.
[11]《文選》卷五九《頭陀寺碑》,《六臣注文選》,中華書局,1987年,第1089頁下-第1090頁上。
[12]對這一命題的思想史分析,參見葛兆光《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對儒家知識世界的擴充與挑戰》,《史學月刊》2011年第1期,第20-32頁。
[13]高麗本作“惟”,此從宋、元、明、宮本。
[14]沈約《答陶華陽》,《廣弘明集》卷五,t52,no. 2103, p. 122, b22-c3.
[15]《晉書》,卷三四《杜預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1031頁。
[16]沈約《均聖論》,《廣弘明集》卷五,t52,no. 2103, p. 121, b24-p. 122, a9.
[17]參見拙文《梁武帝與僧團素食改革》,《中華文史論叢》,2013年第3期,第93-121頁。
[18]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張君房撰《云笈七籖》卷一〇七,李永晟點校,中華書局,2003年,第2327-2328頁。
[19]《真誥》卷一五《稽神樞》,趙益點校,中華書局,2011年,第231頁。另外兩處見同書卷一五《闡幽微》,第269頁。
[20]《辯正論》卷五:“阮氏《七錄》、王家《四部》、《華林遍略》、《修文御覽》,陶隱居之文、劉先生之記,王隱、魏收之《錄》,楊玢、費節之書,並編年紀,咸爲代曆。莫不共遵正史,曾無異談。”(t52, no. 2110, p. 521, c2-6) 對此諸書之解說,參見拙文《〈歷代三寶紀〉三題》,《文獻》,2016年第5期,第127-134頁。
[21]《史通·六家篇》,浦起龍《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頁。
[22]《梁書》卷四九《吳均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699頁。《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中華書局,1973南,第956頁。
[23]庾信著,倪璠注《庾子山集注》,許逸民校點,中華書局,1980年,第113-114頁。
[24]關於重雲殿的結構和梁武帝在此的講經活動,參見chenjinhua, “pancavarsika assemblies inliang wudi’s buddhist palace chapel,” 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06), vol.66 no. 1, pp.43-103.
[25]各個版本的大藏經中收錄的《歷代三寶紀》在《帝年》的截止處並不一致,宮本排到了仁壽三年癸亥,宋元明三本則排到大業十三年隋代截止,高麗本不僅年號排到武德元年以下,而且在開皇十八、十九、二十年分別標注了當年的史事。這些都晚於費長房上進此書的開皇十七年。
[26]《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3, a16.
[27]章巽《法顯傳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第130-131頁,及第133頁注33。
[28]《歷代三寶紀》卷七,t49, no. 2034, p. 71, b25-28.
[29]《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3, a18-19.
[30]法經《眾經目錄》卷六,t55, no.2146, p. 146, b13.
[31]《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5, a12-17.
[32]《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5a21-p.26, a2.
[33]《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3, a20-25.
[34]巴利文本現存,學者研究指出,漢譯并非嚴格對應,尤其後半屬於抄譯的性質。參見水野弘元監修《新仏典解題事典》,東京:春秋社,1966年,第110-111頁。
[35]《歷代三寶紀》卷一一,t49, no. 2034, p. 95, b20-c17.
[36]《善見律毘婆沙·舍利弗品》:“次第從師受持不忘者,優波離從如來受,陀寫俱(dāsaka)從優波離受,須提那俱(so?aka)從陀寫俱受,悉伽婆(siggava)從須那俱受,目揵連子帝須從悉伽婆受,又栴陀跋(ca??avajji)受,如是師師相承,乃至于今。”(t24,no. 1462, p. 716, c25-29)
[37]關於淨秀的生平,參見沈約《南齊禪林寺淨秀尼行狀》(《廣弘明集》卷二三)及《比丘尼傳》卷四。
[38]《出三藏記集》卷一一,第419頁。
[39]參見pachow, “the study ofdotted recor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oriental society (1980) 3:342-439. 轉引自紀贇上揭文。
[40]《开元釋教錄》卷六,t55, no. 2154, p. 536, a7-9.
[41]諸本引文皆作元年,唯《開元釋教錄》卷六引作“大同九年”(t55, no. 2154, p. 535, c27-28).
[42]《歷代三寶紀》卷一一:“推至梁大同九年癸亥歲,合得一千二十八年。房依伯休所推,從大同九年,至今開皇十七年丁巳歲,合得一千八十二年。”,t49, no. 2034, p. 95, c12-15. 另注意此處推算者名字作“趙伯休”,而非“趙伯林”。
[43] jan nattier, once upon a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asian human press,1990. pp.27-64. 劉屹《法滅和末法:兩種佛滅之後的末世論》(“中古宗教史的回顧與展望”工作坊,浙江大學,2016年)梳理了日本相關的研究,尤宜參考。關於末法思想的興起,筆者本人亦擬撰文探討。
[44]《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八《比丘尼犍度》:“為敬法故,若度女人出家,正法只得五百歲住,由佛制比丘尼八敬,正法還得千年。……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學法,復得五千歲。於五千歲得道,後五千年學而不得道,萬歲後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有袈裟法服而已。”t24, no. 1462, p. 796, c21-p. 797, a1. 嚴格地說,《善見律》並未給出正、像、末三時的明確跨度,但卻暗示了正法由制八敬法還復千年,以及萬年以後佛法滅盡。考慮到費長房說“準三藏教”,或許當時有人據此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另外注意吉藏《法華玄論》卷一〇:“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出祇洹精舍碑,《善見毘婆沙》中亦有此說。”t34, no. 1720, p. 450, a1-3.
[45]有敦煌殘本p.2587,末尾多出道安之上奏文,參見饒宗頤《法京所藏敦煌群書及書法題記》,《饒宗頤佛學文集》,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501-504頁。
[46]道宣記載甄鸞上笑道論在天和五年,當年五月十日,武帝集群臣議,道安又上《二教論》。參見《廣弘明集》卷八,t52, no. 2103, p. 136, a29-b2.
[47]“董奉忠”,《歷代三寶紀》作“董奉”。案:董奉及董奉忠,事蹟皆無考。
[48]“至今”,《歷代三寶紀》作“至今天和四年”。
[49]道安《二教論》,《廣弘明集》卷八,t52,no. 2103, p. 142, a14-20.
[50]參見富世平《大宋僧史略》卷上“佛降生年代”條,中華書局,2015年,第2-12頁。
[51]《長阿含經》卷四,t01, no. 1, p. 30, a22-29.
[52]《漢書》卷二一《律曆志上》:“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中華書局,1962年,第974頁
[53]查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依《周曆》推是七日,依《魯曆》推是六日。齊魯書社,1987年,第127頁。
[54]《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3, a27-b13.
[55]《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p. 23, c8-10.
[56]《十八部論》卷一《分別部品》:“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城名巴連弗。時阿育王,王閻浮提,匡於天下。”(t49, no. 2032, p. 18, a9-10) 參見lewis lancaster, "the dating of the buddha in chinesetradition," heinz bechert, ed. thedating of the historical buddha. die datierung des historischen buddha, i, vandenhoeck & ruprecht gmbh & co kg, 1991.p.455.
[57]費長房所撰《歷代三寶紀》是記載真諦生平的重要史源,參見船山徹《真諦の活動と著作の基本的特徵》,《真諦三藏研究論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9年),第1-86頁,特別是第1-4頁;拙文《干戈之際的真諦三藏及其門人》,《哲學門》待刊。
[58]《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t50, no.2060, p. 485, b12-20.
[59]《續高僧傳》卷二三《曇無最傳》,t50, no.2060, p. 624, c16-p. 625, a15.
[60]參見諏訪義純《中国中世仏教史研究》,大東出版社,1988年,第241頁注6。孫齊注意到《續高僧傳·智炫傳》記載周武帝時智炫與張賓論佛道二教已提到“姜斌犯法,此又甚於眾僧”,此事或許在北魏實際發生過(《唐前道觀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第206頁)。但曇無最所引據之《周書異記》等,確實要到《破邪論》中才第一次完整出現,因此仍將其成立下限定在武德五年。
[61]關於法琳《破邪論》的成立,李猛指出上啓的年代和卷數存在關鍵性的異文,很可能傅奕言論始出,法琳立即批駁,形成一卷本,與文獻所見“可八千餘言”、“三十餘紙”的篇幅相當,後來又有所增補。參見李猛《抑佛與護法:唐初抑佛政策演變與僧團回應》第九章“尊道抑佛政策之下的護法論著編撰”,復旦大學博士論文,未刊稿,第242-245頁。筆者將此書成立下限定在武德五年,乃因該書卷下有“自滅度已來,至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t52, no. 2109, p. 484, b28-c1)之語。另外,此書在文獻學上還存在一些不明之點,比如上、下卷的分卷,高麗本與宋元明宮亦不相同。
[62]《辯正論》卷五,t52, no. 2110,p. 521, c6-21. 論中所開列的各種史籍、曆書,解說參見大內文雄《南北朝隋唐佛教史研究》,法藏館,2013年,第145頁及注釋。
[63]礪波護著,韓昇譯《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27頁。
[64]《辯正論》卷四,t52, no. 2110, p. 550, b19-21.
[65]李猛前揭論文,第250-254頁。
[66]《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彥琮序,t50, no.2051, p. 198, b4-5.
[67]《開元釋教錄略出》卷四:“明勅禁斷,不許流行,故不編載。然代代傳寫之。”(t55, no. 2155, p. 746, b16-17) 敦煌本5件:p.2640va, p.2640vb,p.3901, p.3686, p.4867.
[68]關於此書的成書經過,參見陳士強《大藏經總目提要(文史藏)》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79-384頁。
[69]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中華書局,2014年,第261頁。
[70]《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中華書局,1974年,第3027頁。
[71]《續高僧傳》卷二三《曇顯傳》,第903-904頁。
[72]《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第263頁。
[73]《歷代三寶紀》卷一,t49, no. 2034, p. 23, a17-18.
[74]“入”字疑是“人”之誤。
[75]《破邪論》卷一,t52, no. 2109,p. 478, b6-28.
[76]許理和著,李四龍、裴勇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8-489頁。
[77]《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第262頁。
[78]《續集古今佛道論衡》,t52, no. 2105, p. 398, a28-b2. 案:達摩鬱多羅即法上,《開元釋教錄》卷一〇:“高齊眾經目錄。注:武平年沙門統法上撰,梵名達摩鬱多羅,一卷成。”(t55, no. 2154, p. 574, a10)
[79]《續高僧傳》卷二三《曇無最傳》,第900頁。
[80]《辯正論》卷五,t52, no. 2110,p. 521, c26-28.
[81]《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二,t52, no.2106, p. 415, a12-14.
[82]《南嶽思大禪師立誓願文》,t46, no.1933, p. 786, b27-c6.
[83]湯用彤注意到莊王十年並非甲寅,而未考慮甲寅乃受昭王系學說之影響而成立。張總發現《立誓願文》與此說都以癸丑入胎,甲寅佛誕,而未注意二者王統紀年不同。張總先生進而認爲慧思乃據《後漢書》結合餘說而成。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頁。張總《末法與佛曆之關聯初探》,《法源》第17期,1999年,第144頁。如果觀察此說雜糅莊王、昭王兩系學說的性質,以及該說由類書所引,推定這條材料後起於昭王系學說比較合理。
[84]《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中,t50, no.2051, p. 207, c3-9.
[85]案:此經《祐錄》、《法經錄》等皆著錄“失譯”,唯《歷代三寶紀》著錄聶道真譯。david quinter認爲經文的內容與觀經類經典有諸多關聯,因而將經文成立年代定在4-5世紀之間。詳細論證及全經英譯,參見”visualizingthe ma?ju?rī parinirvā?a sūtra as acontemplation sutra,” asia major,third series, 23, no.2[2010], pp. 97-128.
[86]《文殊師利般涅槃經》,t14, no. 463,p. 480, c20-23.
[87]《歷代三寶紀》卷二,t49, no. 2034,p. 30, a14.
[88]《破邪論》卷二,t52, no. 2109,p. 484, c23-26.
[89]《曆代法寶記》已收入《大正藏》第51冊,柳田聖山《初期の禪史》(ii)根據9件敦煌寫本做了錄文和校勘。榮新江又陸續找到了3件寫本,《敦煌本禪宗燈史殘卷拾遺》、《有關敦煌本曆代法寶記的新資料——積翠軒文庫舊藏“略出本”校錄》,并見《辨僞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3-1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