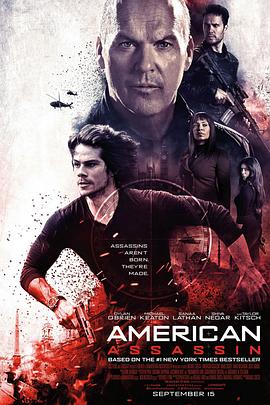剧情介绍
罗伯特·弗兰克教给我的那些事
撰文│廖伟棠
自从一年多前搬到新居,我家离机场更近了,但去坐飞机远行更少了,我常常在夜深孩子熟睡后拿一罐啤酒站在阳台,看飞机平均三分钟一班地爬升。别眨眼,我凝视着黑暗,好像十年前的我凝视着今天的我。
最近看的电影,最感触良多的,是一部关于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的纪录片《别眨眼》(don’t blink - robert frank),因为它让我反思我的生活之去向问题。
罗伯特·弗兰克是在摄影美学上影响我的首屈一指的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的历史是一个流浪者的历史,同时也是二十世纪视觉观念革命的同生史:他五十年代拍摄的专集《美国人》被视为记录摄影的转折点,严重颠覆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奠定的“决定性瞬间”准则。他的照片也是存在主义式的。
我的第一本摄影集《孤独的中国》无论选片还是排版都是向他的经典《美国人》致敬,而且我曾经想以自己的生活向他致敬——学习他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摄影师、垮掉一代最后的浪荡子,只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
很明显,我没有做到,人在香港身不由己,渐渐也活成一个“稳定”的人,家庭成为一个重要的借口。《别眨眼》里面那个不迁就世俗、狂狷独行的老头子,仿佛离我越来越远,收拾一个破挎包带上一部老菲林相机就出门远行的日子越来越少。但是十年前,我这样做过。
我从《良友画报》辞职,忽而就十年。《良友画报》高级编辑,那是我最后一份正式工作,十年过去,生涯浩荡,再也回不到任何羁绊中去。加入《良友画报》,是因为慕其名——毕竟是中国第一份摄影画报,感觉自己加入了历史似的。
但现实又不是那么回事,《良友画报》经过两次停刊,再生乏力,投资者也并非杂志中人,年轻的编辑记者于其中不过混饭等死而已——起码离开它的那一刻我是这么想的。
看似与追求自由相反的是,那年我还结婚买了一个小房子,想来这完全不合乎常理,彼时我和妻子双双失业,靠每月不固定的稿费以及妻子做补习老师为生。
开始的时候我和内地一本著名的青年文化艺术杂志有比较如意的合作,为它拍摄每期过百页的外国城市专题,但是好景不长,据说赞助拍摄的外国旅游部门越来越少,杂志就倾向聘用当地摄影师或者直接购买成片了。
其后,渐渐我接了不少案子,其实是一点都不想拍摄的,时尚人士的采访、美食、酒店??一天猛然惊醒,所谓的自由摄影师并不自由,因为作为作家、诗人的我是一个反消费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垮掉派,怎么可能违心去美化自己反对的事物?
讽刺的是,我的相机也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把那些美食都拍成了暗黑料理,把那些成功人士都拍成了黑社会??于是,我光荣告别时尚摄影事业。
五年后,儿子出生,他成为我最好的狱卒,让我更难离家半步,当时感言“人生中第一次自愿失去自由”,不幸言中。这是爱吗?我理解的爱应该是彼此成全自由——但你又怎么可能向一个小孩解释你所需要的自由?
罗伯特·弗兰克都做不到,电影里看到他女儿二十岁死于飞机失事、他儿子四十岁死于癌症,罗伯特·弗兰克万念俱灰,我只想对他说:你已经尽力了,你本应像你的老友杰克·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一样只为自己活着的。
如今我无愧于十年前的选择与承担,即便里面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而我又更期待十年后、二十年三十年后,因为我在八十岁的罗伯特·弗兰克身上看到了真正的自由。我竟然不纠缠于青春的残余,而向往起老年来了。
中年是炼狱,你甚至没有引路的维吉尔。看完《别眨眼》,这名字让我想起十年前罗伯特·弗兰克的一本书名《hold still-keep going》,这句话在今天更应该成为我的座右铭吧,再加上《别眨眼》,沉静、永动、火眼金睛,这是穿越炼狱的秘诀。
走出铜锣湾皇室戏院,没有走入地铁站,而是右拐入了维多利亚公园,维园夜雾,人已寥寥,面对灰蒙蒙的一片树影,我掏出手机打开拍摄app,因为我又感到右手食指在雀跃欲痛击快门——别眨眼,我凝视着黑暗,十年后的我凝视着今天的我。
编辑│晓风
(除去首图,所有图片来源于罗伯特·弗兰克摄影集《美国人》)
更多精彩原创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兰阇(qdlans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