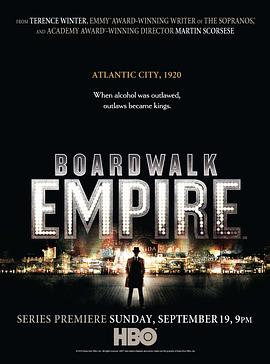剧情介绍
或早或迟,春天总是会来的,一年又一年。
当清明前渐浓的春意被阴郁的雨天打断,望着窗外愁云凄风的我突然更加怀念一个人,突然又想去重温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某个小小房间里,那异常寒冷的春天。
一直在说《春光乍泄》于我个人有着里程碑一般的意义,只因为那里的何宝荣是我对哥哥从演技到品行到音乐到一切一切全面且压倒性溃败的开始:因为哥哥的何宝荣,我中邪一般地对《春光》反反复复重温无数遍,妄图挖掘出这个台词与戏份都实在不多却不知为何死死攫取住我所有视线的角色心里所有从未言明的感情;因为哥哥的何宝荣,我人生中头一次码出那么多文字的感慨,一遍一遍的推敲,一遍一遍的修改,一遍一遍的补充,一遍一遍的以为自己终于淡然放下,却总在熟悉的音乐中,又一次体会心底的隐痛。在反复的添补与修改中,我发现那篇会永远置顶的博客也许真的已经无法承下更多散碎的文字。于是干脆另开一篇吧,在《摄氏零度·春光再现》里,把零散的感慨罗列出来,作为《一层胸壁的距离:这么远 那么近》( )的补充。在2015年4月1日——哥哥离开整整十二个年头的这一天,我想以这些文字给自己留下也许不会增添更大遗憾的记忆。
不同于《春光乍泄》,第一次看这部记录片后,我好久都不敢再重温 :在这个现实的记录与带着浓重胶片味道的电影片段相互交错的叙述中,短发的妹子ailin带着记录镜头重游故地,当毫无心理防备的我随着她的脚步走上熟悉的楼梯,走进那个已经没有了门的房间,看着那个已经冰冰冷冷的房间,那个箱柜堆叠得凌乱却只让人觉得空空荡荡的房间,
一瞬间,所有关于何宝荣的记忆像突然泻了闸的洪水一样在我脑中涌出——他的巧笑娇嗔、他的撒娇耍赖、他的沉默凝望、他的愤怒宣泄,他的一切音容笑貌本应鲜活在那间本该有着暖暖灯光、有着家的温馨味道、有着一个被窝里拥挤的两个脑袋瓜的小小房间的每一处角落里,
可这一切一切,再也没有了——
于2014年回看那个属于1999的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房间的我知道,一切的一切,再也没有了,也永远无法再重头来过。这一瞬间涌来的巨大感伤塞满了我的大脑,以至于我木然地呆坐在屏幕前,对后面墨镜一个比一个更加风中凌乱的脑洞构思无知无觉。
“stuck”在《春光》很长时间还是没能走出来,我觉得也许心里这种满满的伤感甚至委屈也许应该用文字宣泄出来。于是为了书写对《春光》的感慨,我才再次打开《零度》,希望换个角度,在对比这些被墨镜凌乱涂鸦勾勾画画,最终揉成一团扔出个完美抛物线的草稿中找出他想表达的东西,或者更无耻的说,在他最终的取舍对比中牵强附会出我心里想要的故事——一个更让我欲罢不能的何宝荣。
下面的文字里,我就用《春光》与《零度》分别标记电影正片与记录素材吧。春光总给人暖暖的感觉,而摄氏零度则是一个微妙的分界线,水可以结成冰,冰可以化成水,冰水相合,有无限的可能。
【甜蜜】
小屋天台上,伟仔原来还有扑倒哥哥,从流出的工作照还能猜得出,连俩位影帝滚来滚去的姿势恐怕都是墨镜亲力亲为做示范过的。可即使是这样费劲拍摄的素材也没有纳入正片中。《春光》里,对宝宝的亲昵的回应从滚屋顶变成了冷冰冰的背对背——阳关灿烂的天台,宝宝望着天,木头看着地,俩人再无互动。这之后,迎来了何宝荣再一次(我总认为也是最后一次)的离开。
这样把甜蜜一个个舍弃而作的铺垫,让何宝荣每一次的离开更加容易理解了吧。
【绷带】
宝宝绑在手上的绷带是我非常注意的细节。总觉得其实宝宝的伤早就好了,但他一直缠满绷带,给自己也给木头一个理由一直撒娇耍赖被木头宠溺着(所以每次木头放狠话宝宝就惨兮兮举双手问他“我都这样了,你舍得?”)。天台之后,宝宝彻底退去了绷带,我想那是他也终于认命俩个人还是无法再在一起的时候吧。
在《零度》里,还有处甜蜜的细节就是小房间里电视坏掉,宝宝吵着让木头修,小小的电视机前宝宝搂着木头,俩个人恩恩爱爱。很多人也怨念这样温馨的细节为什么不放入正片里,我想如果按我的理解仔细看宝宝的手,就解释通了:
那个片段里,宝宝手上没有缠满绷带。
在我眼里,宝宝的绷带像一般情侣的对戒,他总是带着委屈又带着炫耀甚至还夹杂着威胁的对木头举着缠绷带的手,默默宣誓着爱情,也是在寻求着更多的宠溺——尽管木头从未对他说过他受伤的日子是木头最开心的时光。
我想,如果木头没有总是放不下宝宝过去的那个心结,宝宝会不会一直缠着绷带腻着木头,一起,去看瀑布呢?
【占有欲】
“在记忆里面的感觉是潮湿的,整个房子都是软软的,生命感好严重,好像有生命,可是有点生病,不晒太阳的感觉。”
在《零度》里,我很喜欢那个叫ailin的短发妹子,喜欢她对那段回忆这样传神的描述,也喜欢她对身处异国他乡的态度:
“常常是自己一个人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去,那种好像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知道我的历史,那种感觉是自己很喜欢的。”
顺着这个思路看下去,我发现磨人的小妖精何宝宝其实有着比黎耀辉强得多的霸道总裁般的占有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