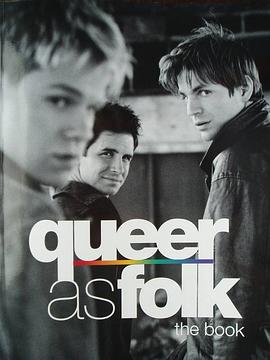剧情介绍
如果你认为进化论“只是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坚实的证据支撑——读读这本书吧,收获新的认知!
如果你从来不晓得达尔文曾与蠕虫喃喃低语,以及他作为种子魔法师,蜜蜂助手等其他多重身份——读读这本书吧,享受这种邂逅!
如果你怀揣着对科学及其运作方式的热忱,并准备好开展力所能及的创造性工作——读读本书吧,激发更多的热情!
总而言之,读读这本书吧——《达尔文的后花园:小实验如何撬动大理论》。
这本书透过独特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达尔文:他既是一位热情洋溢的记者与合作研究者,更是一位不可救药的观察者与实验者。
实验家的养成
达尔文在十一二岁时的绰号是“毒气”。当然,这个名号并非来自肠胃气胀,达尔文的同学因其对嘈杂、难闻的化学实验的嗜好而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达尔文和哥哥伊拉斯谟会在自家漂亮的红墙宅院花园后的临时“实验室”中做这类实验。
被他们唤作“实验室”的地方离学校仅有几步之遥,达尔文很容易就能将吹管和化学制品带回宿舍,然后在就寝时间后对着煤气灯做“实验”,直至校长塞缪尔·巴特勒对此有所耳闻。达尔文从未忘记自己被公然贴上“屡教不改”的标签(意即肤浅的涉猎者,而他认为这并不公正)时遭到的谴责。
剑桥:甲虫、植物研究和地质学101
达尔文在剑桥大学度过了3年时间,有那么一段时间,达尔文生活在一群精神饱满但胸无大志的富家子弟中。
他后来感叹道,自己在剑桥的时光“比浪费还糟糕”,但他当时也有些迷茫。
最终,他受当时同在剑桥上学的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的影响,发现了搜集甲虫的乐趣,这种爱好看似毫无意义,但给达尔文带来了生物多样性和变异的直接经验。
“搜集甲虫是我在剑桥最热衷且最令我感到快乐的爱好。”达尔文在其自传中如此写道。他的朋友阿尔伯特·韦在其名为“骑在巨型甲虫上的达尔文”的漫画中,对达尔文这种痴迷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
实际上,搜集甲虫对达尔文不只是一种乐趣:它几乎还是一项流血的活动。置身于求胜心切的甲虫搜集者之列,达尔文差点儿就对自己出钱雇用的甲虫搜集者大打出手了,因为他发现那个无赖让竞争对手优先挑选了自己找到的宝贝。
他对甲虫的狂热也可能是危险的,就像他在给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德·杰宁斯的一封信中谈到的情形一样:
但如果说搜集甲虫教会了达尔文某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从而让他更好地处理解剖结构和物种变异的细微之处,那这两种习惯也都受到他在剑桥的另一种爱好的强化:采集并研究植物。
抵达剑桥的次年,达尔文遇到了数年前就成为植物学教授的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牧师。
达尔文成了亨斯洛每周乡村植物行的常客,并因此被称为“那个与亨斯洛同行的人”,还受到亨斯洛夫人及其孩子们的欢迎,因而成为经常前去与他们共进晚餐的座上宾。
亨斯洛重新点燃了达尔文早先对微观分析和探索的热情。亨斯洛的植物学教导方法教会了达尔文“专注”并欣赏复杂的结构和个体差异,他还让达尔文理解大局:全球范围内的哲学植物学,它旨在获悉物种可能出现的地理分布模式。
但他在达尔文的地质学教育中发挥的最重要作用是将其介绍给剑桥大学的教师亚当·塞奇威克牧师。
塞奇威克和亨斯洛一样喜欢与学生们一同到野外郊游,有时会带领60人或者人数更多的马队穿过乡间,然后在沿途裸露的岩石或者其他地质构造上停下来开讲座。而在暑假,他就开展自己的田野调查。幸运的是,那一年他进入了离达尔文家不太远的北威尔士。塞奇威克对追随自己的达尔文尽职尽责。
达尔文与塞奇威克于8月5日起程前往威尔士以继续达尔文已经延期的“地质学101”课程。此次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确定裸露的老红砂岩的具体位置并绘制地图。
老红砂岩是塞奇威克此前已确定属于泥盆纪(devonian,实际上他早已为这一地质时期创造了这个名字)的沉积构造,根据现代科技测算,泥盆纪距今3.59亿-4.19亿年。
二人并未找到老红砂岩,但达尔文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野外地质学知识。到了考察的最后一段,他们便分头行动,以探索更多地方。达尔文往南前往巴茅斯看望朋友,途中在位于斯诺登尼亚山脉甘德劳山峰异常美丽的科沃姆·艾德沃尔悬谷短暂停留,此处无比清澈的湖泊背靠名为“魔鬼的厨房”的巨大石壁,大量漂砾点缀其间。
达尔文在此做了一番考察——又多次颠倒了指南针读数——然后忠实地将结果写在信中告知塞奇威克。
塞奇威克回信纠正了一些他认为的达尔文对某些地质构造的误解,但总的来说,达尔文作为一名地质学学生仍旧表现出色(尽管他在10年后回到科沃姆·艾德沃尔时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多少东西,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接着,达尔文在看望了朋友之后便起程回家,亨斯洛的来信已在家中恭候多时。加那利群岛之行惨遭取消。不过,亨斯洛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加非凡的冒险机会:做一个环球航行中的绅士博物学家。
达尔文的远航
“小猎犬号”在达尔文尚未克服晕船之际便已离开了普利茅斯港。同船的人可能会告诉他,他很快就不会晕船了,但很遗憾,他在整个航行过程中都有些不适,而从科学史的角度往回看,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迫使达尔文一有机会就离船上岸。(事实上,在近5年的航行过程中,达尔文总共仅在船上待了一年半左右。)
因此,即将停靠特内里费岛的可能性无疑给达尔文带来了双重喜悦——一来可缓解呕吐的症状,二来终于有机会看到洪堡曾热情赞颂过的景致。瞧,圣克鲁兹港口已隐约可见。
遗憾的是,英格兰地区当时暴发的霍乱阻止了“小猎犬号”的船员登陆。当地政府坚持要求这艘英国船舶检疫12天,但赶时间的菲茨罗伊船长不耐烦地起了锚。船长在他的航行回忆录中提道:“这令达尔文先生大失所望,他曾梦想攀登当地的山峰。
为了看到它,船只得在登岸的地方下锚,然后在尚未得见一星半点特内里费岛的景致时又必须离开,这对达尔文来说实在是场灾难。”不过,圣克鲁兹当局的担忧是有根据的:整个19世纪,接连肆虐世界多地的霍乱等流行病曾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尽管如此,达尔文也不必再苦等更长时间以首次体验热带岛屿:“小猎犬号”于1月中旬访问了佛得角群岛,而就在其中的圣雅戈岛,达尔文注意到一处醒目的景致:嵌入悬崖壁、距海平面约13.7米的白色贝壳带。
他现在正从赖尔的视角看待这一现象:海贝一定是逐渐向上累积的,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运动肯定会破坏近乎水平的贝壳层。这种观点与赖尔“漫长时期中的缓慢变化”这一理论相符。达尔文写信给亨斯洛说:“(圣雅戈岛的)地质十分有趣,我确信它形成的时间很晚:此处存在着一些海岸大范围抬升(这是火山岩源起的极佳时期)的证据,赖尔先生可能会对此感兴趣。”
这是他永生难忘的时刻:他首次考察的地方证实了“相较于其他任何他曾经阅读过,或者后来阅读到的其他作者的方法而言,赖尔的地质学方法具有非凡的优越性”。
在剩下的航行中,达尔文以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为指导,针对性地考察了许多地方的地质情况。正如赖尔后来承认的那样,达尔文响应了他的召唤,明白了新科学的见解和概括可能仍有其局限性,但“它的追随者渴望获得我们劳作的最宝贵成果。同时,在我们探索这个宏伟的研究领域时,首次发现的喜悦属于我们自己……”
尽管达尔文越来越将自己视为地质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史的其他方面疏于用功。他首次在爱丁堡见到的那些神秘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就像一张深邃的网一样吸引他的注意力。
在锚地之间的公海区域不受晕船的困扰时,达尔文常常会打开自己那张捕获浮游生物的网,看看能发现什么样的海洋生物——根据他记录的第二张网的使用情形,他很可能从罗伯特·格兰特那里学会了织网的手艺。
达尔文捕获了大量海洋微生物,“相对于大自然的规模而言,它们是如此渺小,却有着无比优美的形态和丰富的色彩”,他在日记中写道。随之而来的是意料之外的反思:“如此之多的美丽生物明显是为十分渺小的目的而生,这真是一种神奇的感觉。”
毫无疑问,“小猎犬号”的探险之旅带来了大量实地采集与观察的成果。在达尔文的《“小猎犬号”航海记》中,“观察”或“查看”等词出现了73次,“检查”一词则出现了48次,而“实验”一词仅出现了4次。
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远航过程中的早期“实验”可能连玩儿带做就完成了,但它们仍体现了一种渴望调查、经验和学习的质疑心态。
扔海鬣蜥的达尔文也正是那个敏于察觉任何有趣或不寻常的情况,从而将自己的发现、思考和观察写满一本本笔记本的达尔文。例如,他不停地抛出捕获浮游生物的网(这比捕捉海鬣蜥来得容易),并惊叹于所得的收获,想象着某天能出乎意料地在遥远的大海上捞上一网甲虫。
人们可能会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那些甲虫在广阔的海洋中干什么呢?之后,他会意识到此类平淡无奇的观察结果对于理解地理分布十分重要。
另外,达尔文在里约热内卢附近又采集了一些菌类,它们看上去与家乡的类似。他思忖着这个来自欧洲的物种如何能吸引甲虫,就仿佛此刻恰好有一只甲虫飞来落在他手中的菌类上。与澳大利亚蚁狮的情况一样,“我们由此看出两个遥远国度的同族植物、甲虫之间的相似关系,尽管这两个物种本身是不同的”。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达尔文对这一切都充满了惊奇:他会惊讶于“蜘蛛在空中飞行”,无数幼蛛成群结队地在船只索具上的轻薄蛛网上穿行,一阵微风很容易就能把蛛丝吹走;也会惊讶于巴塔哥尼亚北部沿海地区“蝴蝶如雪片般落下”的惊悚夜晚,当时,这些“数量众多”的昆虫“成片状或絮状纷纷落下,范围远超目之所及”;更会惊叹于南大西洋上“壮丽的烟火”,圣埃尔莫之火照亮了桅杆和横桁臂,整个海面“变得明亮无比,甚至连企鹅的行踪都因为燃烧的尾迹而变得清晰可见”。
一部有血有肉的巨匠生平,
一段妙趣横生的发现之旅;
看一部伟大的经典如何诞生,
看一个伟大的理论如何成型
上一堂原汁原味的大师课,
看达尔文如何一路打怪升级,逐章攻克难题。
【淘宝】https://m.tb.cn/h.5ppomam?tk=iijewe7yqrw cz3457 「【精装】达尔文的后花园 小实验如何撬动大理论 生物学书籍正版图书」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